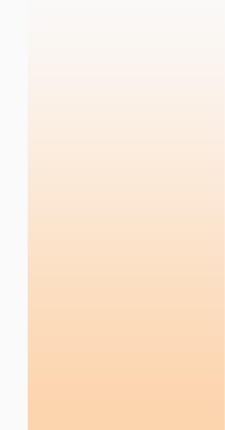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成立王仁璐專區 |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成立王仁璐專區 |
 |
王仁璐在“王仁璐贈書開幕典禮”的致詞 “一位藝術家的生命歷程照映:傳承,多元及智慧的典藏” PresidentZhu朱校長DeanPing平院長DeanWang王院長YingGuanZhang閻館長 謝謝你們的引言,在中華民國慶祝百年壽辰的時刻,這個典禮可以說也是一個歷史的事件。 在這些原住民族的所有生命禮儀的場合——如生育時、婚禮、喪事、種植及收穫——歌舞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動。舞蹈與歌唱在空氣中迴盪當然滋養了我。所有這些早歲的影響令我深信這樣的歌舞是神聖而天成的、真摯的對人生的肯定。 藝術家不是孤單的個人;每一個藝術家的途程都受到無數貴人與大師的教養和扶持。 我的雙親是我的第一對貴人。他們是在清朝出生的。母親魏君眉富有藝術天才,她能吹奏笛子也是有天份的畫家,雖然她只在私塾受教,她學過英語,也學過穿跑鞋打羽毛球。 她的雙親是戲曲的愛好者,常帶她到紹興的水上戲團子聽戲,也不時包了大船,帶全家看「滴咚版」;家人們大多能哼上幾句越劇,尤其是《梁山伯與祝英台》這個戲目。但是做為當時的女性,我母親亦有她倔強反抗的一面。 依照那個時代的習俗,她長到六歲就得纏足,但是她盡力逃避裹小腳,每晚偷偷把縫的線拆掉,把包腳布條藏到不同的地方。有時候藏在灶頭土地公後面;有時候藏在閣樓上。如此延續了一星期又一星期,大人被她氣死了,不但要再去買那麼貴的裹布條,更糟的是腳一寸又一寸的長大,最後不得不放棄。雖然她腳中的骨頭沒有全部被折斷;但是已造成她終生走路都有困難。 抗戰時間我父親王振芳擔任了昆明中國銀行經理。當時所有用以支持全國財政和戰時經濟所需的外匯都必須經過滇緬公路,從印度以卡車運到內地;路上經過很多原住民族的地區 當局政府對待原住民族老百姓卻驚人的粗暴,當地的老百姓為了抗爭免不了使用破壞長途行駛的載運卡車的手段。 我父親手上的卡車有限,他知道外匯對整個國家的重要性;為了保護外匯他必須贏得當地百姓的民心。為此,他派了醫事人員進駐,治療天花、提供醫療;最後終於取信於原住民族的老百姓。我出生時,他為了紀念這一段有意義的關係,為給我取名大費腦筋。因為當時的人將原住民族通通稱為「裸裸人」——這當然是輕蔑性的稱呼。父親要我的名字聽起來類近,但又不是歧視性的;他於是在「路」這個字加上了女性化的斜玉旁,成了我名字上「璐」這個字。 抗戰勝利後,我父親被派到中國銀行廣州分行當經理。在廣東省省主席宋子文下服務。1949年他受命將所有中國銀行的資產轉移到香港。於是不得不把整個家都帶到了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管理下的香港,所有的教育機構幾乎無不是交給各宗教團體,及各教派的傳教單位辦理。到香港時,我剛念完二年級。因為所有的學校都被逃難的外地人擠滿了,只剩下一間加拿大人辦的、教法語的聖嘉勒小學有五年級的空位。我就這樣被塞了進去。就這樣,我從二年級一下跳到五年級。但當時我所會的英文恐怕只有幾個字母。而所有課都是用英文上(法國修女講的則是法式英文),唯一不是用英語教的課是中國古文課。還好那時因為我已在廣州住過,已能講流利的廣東話。我母親則必須每晚幫我做功課。她聽我用上海廣東話背四書;當我站在課堂上也一樣地背的時候,大家哄堂大笑,笑我的上海廣東話。所以我的古文科永遠是不及格的!!儘管我的中文、英文都學得不怎麼樣,我倒讀了不少家裡的古典文學;當然,以三年級左右的程度,讀不大懂《紅樓夢》;但我愛上了書裡的插畫,深深被書裡各式戀人、官員、婢女吸引,也對各種花木、蟲鳥的描寫感到極大的興趣。 念完中學後,我父親期望我做醫生。送我進美國麻省有名的Tufts University大學醫預料,希望可以直接保送入醫學院。這時我十八歲,已經不能繼續瞞著我父親偷偷去Rober tCohan的NewEngland Conservatory o fMusic上舞蹈課。當我終於向父親要求要改行投入舞蹈,並拜Graham為師時,父親問我這個決定是否在多方面詳細有過深入的思考,而不是一時幼稚的衝動或浪漫的幻想。我肯定地給了他我的答覆。之後,我這生從來沒有否定過,也沒有後悔過這個決定。那時,我父親人在香港,就請我叔叔王則甫到紐約去拜訪Graham。叔叔回報?:”Graham是世界第一流的藝術家,深受愛戴與認可,只是跟他學習的那些舞者都不穿鞋子,光著腳實在太怪、太髒了!” 我珍惜在計畫中與突尼西亞、迦納、澳大利亞及加拿大等地同事們的長期合作經驗。典藏中的另一部分是和史密松學會的美國民眾生活節有關:特別是1976年的美國建國兩百年,在首都華盛頓的慶典。在這個國家首都的心臟地帶,來自尼泊爾及至芬蘭的各個民俗藝人展演了他們的民族藝術瑰寶,再次地演示了只要人們以她們真摯的發聲舞蹈歌唱,他們就是歡樂地歌頌生命,令人眩目地受到感染。節慶中的一個區塊是題獻給「勞動中的各種美國人」;我從而知道了鐵路工人怎麼建築鐵路的。一群八十多歲的退休築路工人,表演了放置路軌的勞動過程;他們的綽號叫作「鵝舞士」,因為他們一邊勞動一邊齊聲吟唱。這個景象後來構成為了我以華籍鐵路工人勞動創作的「金山」舞劇的歷史根據。 感謝柯達公司慷慨地為節日提供了當時最先進的四架Super8mm電影攝影機,也承擔了全部的軟片及沖洗支出;當時錄下的三十四小時紀錄片現在屬於史密松學會的收藏品了。儘管如此,好消息的是四分之三吋的錄像帶現在是屬於北藝大的了;我希望有機會能把它們數位化,不但北藝大可以用,全台灣和全世界也可以使用到它們。典藏中的這一個獎狀是1968年的教育部文化局局長王洪鈞頒給我的。而我迄今最深為感激的是俞大綱教授,沒有他我今天不會在這裡。當我面對要在四個禮拜內創作一整場發表會而感到踟躕不前之際,他挑戰我說:「哪裡有什麼恰當的時機?抓住這個機會!你還在等什麼呀!」這句話成了我的左右銘。在現在這樣的場合,我知道我的父親是未曾缺席的,我十歲時,他給我一個格言是「學做好人」,這句話也引導了我的一生。 在愛麗絲夢遊幻境的故事裡面,毛毛蟲問愛麗絲「妳是誰呀?」 在一定意義上,所有的藝術家都在問同樣的問題。我替愛麗絲給的回答是:做一位好祖宗。文化局的獎狀稱我作旅美舞蹈家,北藝大圖書館的陳列架上也稱我為旅美舞蹈家,我希望有一天我會是一個回歸舞蹈家。這個回歸,不是回到雲南,而是回頭找到如何走向好祖宗的第一步。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