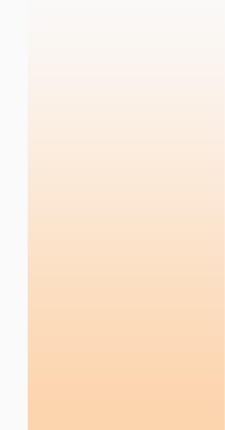|
與仁璐共舞 聶光炎 文 「與仁璐共舞」,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是一段美好的記憶。 一九六八年,我從美國接受劇場專業訓練,回到台灣不久。那時候台灣的表演藝術還停留在「餘興節目」、「康樂晚會」那種趣味的階段,本土「現代舞」創作還沒有個影子,偶而有些歐美文化交換來的演出,則是很稀罕的。仁璐就是在那時接著李蒙、保羅泰勒、黃忠良而後出現的現代舞蹈家與編舞家,著實惹人矚目,無論她的演出或演講,都曾有很大回響。在一次傳統與現代的激辯中,她的「黃酒與威士忌」理論,也很能引起共鳴。我清楚的記得,是在一位美籍交換教授的家庭聚會裡,坐在「榻榻米」席墊上,與仁璐相識、談舞、說戲,而受邀與她共舞。我們真是一見如故,很有緣份,一交就是好多好多年。 我雖然一向為趕熱鬧的「晚會」設計意願不高,但是能有人為「現代舞」出一筆錢,作一次實驗性的演出,實在是挺難得,明知困難多多,我還是興致勃勃的參與了。仁璐的「發表會」中,我主要的工作是設計舞台和燈光,當然在過程之中,因為臨時需要,而擴充到劇場技術執行、服裝材料採購、演出助理、舞台技工到清潔地板· 這樣一個全程下來,我與仁璐之間,深深建立了藝術上的認知與共識、友誼卜的情感與瞭解。我們一道討論、辯論,我們也一起沮喪、歡愉。排演場、d 、緬館、布店,熙攘的街頭、壅塞的公車,仁璐不停的用精細的語言向我解說她的觀念,有時也會手舞足蹈的傳達她的情感。可巧當時我正再讀「鄧肯自傳」,以至使我時時會覺得身邊又出現了一位鄧肯,侃侃而談,翩翩起舞,印象鮮活。同時我也戲嘲自己沒有哥登克雷那樣才華,能為她作出完美的設計。 「雪盟」、「輪迴」、「躊躇」、「蛻進」、「眾相」、舞劇「白娘子」是仁璐那次發表的舞作。基本上,’在舞台與燈光上都有要求,不過「白娘子J 應該算是重頭戲,我設計了一大片彩色背景幕:一條配合舞蹈動作的繩梯,一片象徵塔的景片。極簡單,也很素淨很中性。由於舞台燈光設備有限,而且簡陋,所以在處理上都是「極盡所能」。我必須說那次設計,非我理想的,但確是非常努力的,到頭來也許有一點「少就是多」的成就。在那麼多年前,能作那麼「前衛」的演出,是一件很過癮的事,對一個從事舞台及燈光設計的人來說,面對新觀念、技巧、陳舊思想、簡陋劇場的挑戰,真是一件大事。我總算熬過了。對我來說,那次演出,是一個特殊的經驗,一次學習。仁璐在我創作過程中,給我啟示和激盪,都是很有價值的。當然,她視舞蹈藝術為興趣、事業、生命的精神,也足可鼓舞我執著作劇場設計的理念。 自「白娘子」落幕之後,我和仁璐有很長一段時日不得交往,但我覺得我們心神友誼並沒斷,果不然幾年前再相逢,情份如舊,而她的藝術造詣與修養,真是成長太多。雖然我們還會津津樂道「白娘子」演出的樂事,但我更豔羨她「金山」一舞所發出的生命力與光彩。我也體會到,她的舞作呈現在新的視覺環境下,更為貼切,生動,還遠超過我所能提供的「人工化」,有些做作的舞台與燈光。她選擇在路易斯· 康,堅實、樸素、和諧的建築群之中演出,我感覺到仁璐對文化母體的尊重,對生命的關懷,更覺察她從傳統中鍛鍊出的現代,而不是那種故弄玄虛的現代幌子。我不是作評論的人,不會冷靜分析舞作,我只能熱情的去感覺,那些位舞者急促的呼吸,心房脈搏的跳動,戰慄的肌肉,滾燙的汗水與淚水… 我窺視到編舞者的一份熱愛,用身體與環境建構起一片心靈的大地,豁開了一條長流,淌入文化的過去與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