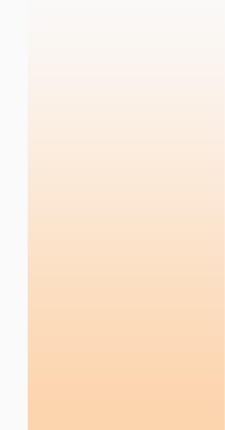|
迎迓中國舞蹈藝術復甦 俞大綱 原載五十六年八月號中美月刊 本期舞蹈特輯,曾蒙俞大綱先生應允撰文並收集資料。不幸於今年五月,俞先生以心疾逝世,本刊特從余先生書房中搜尋出部分圖片及舊文三篇,於本期刊出,並以此敬悼俞大綱先生。 我們今日的「表演藝術」發展中,舞蹈可能是較弱的一環。所謂的「民族舞蹈」,雖經不少人士的積極宣導,似乎尚無成果。「民族舞蹈」一詞,運用得也太廣泛,涵義含混不清,不知是指全中華民族的舞蹈,其中包括主要構成份子的漢族而言呢?抑或僅指少數民族,如苗、傜等民族;或邊疆民族,如蒙、藏、新疆等民族的舞蹈而言。實際上,單就新疆而論,已包括不少不同的民族,他們各有各的語言,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舞蹈程式和風格。把中國舞蹈統稱為「民族舞蹈」似乎嫌廣泛些。 我們所看到的少數民族及邊疆民族舞蹈,只有服裝上的顯著區別可尋,其表達內容,好像沒甚麼兩樣,大部分屬於男女戀愛的抒情舞,很少涉及生活描寫。有之,不過像山地舞的杵舞一類的題材。北方邊疆民族的遊牧生活,西藏民族的宗教精神,前者大漠的磅礡氣勢,後者靈奇的神秘情操,蘊藏著無窮盡的民族活力,足以提供舞蹈藝術的編導題材,但至今還未見有人從這方面著手。 假如說音樂舞蹈是孿生藝術,有舞蹈必須有音樂伴奏的話(其實並不儘然,舞蹈絕對可以獨立表現,只憑肢體的活動,而具有音樂的節奏與韻律美),那末,我們也有年輕的作曲家,如許常惠、史惟亮君等早已採取邊疆民族音樂的旋律和風格而作曲。最近聽到李泰祥君所演奏的小提琴四重奏,標題是「讀唐詩有感」,也頗能抒東方思古的幽情,可以采為舞曲和電影配音,何以我們的民族舞蹈工作者,從來沒和他們合作創造舞劇?只有姚明麗女士曾經和我談過,想用媽祖故事編一出舞劇,並請許常惠作曲。 媽祖題材,屬於倫理的(媽祖在傳說中是一位孝女)、宗教的、也是海洋性的,這類題材,制曲不易,編舞更難。但我們坐令少數民族和邊疆的舞蹈僵化如此,委實是不應該的。這些民族的日常生活和音樂舞蹈,至今還沒有脫節,無論是農作、遊牧、狩獵的生活操作,以及祭神、示襄災、婚、喪等儀式,依然以歌舞來表達個人的和大眾的集體感情,我們還有活生生的題材可參考,再借他們的藝術創作衝動,來構成我們的製作,這條道路是走得通的。遺憾是我們全不去理會他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更不瞭解他們的藝術生活,因之所編的舞蹈,沒有內容,缺少活力,以形式而論,也不分他們的生活是山居或野處,地域不問天南地北,概用類似的舞步和身式,來表現絕不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與情操。更其可怪的,幼稚園的這一類民族舞蹈教材,也和成人表演的同樣組織,那些天真兒童,被裝扮得怪模怪樣,擠眉弄眼的表現男女逗愛調情(所表現的絕不是互相傾訴愛慕的情操)。我想觀眾的感受,必與聽榮星兒童合唱團的兒童聖潔歌聲,成為強烈的對比。 談到古典舞,更令人懷疑。這些舞蹈不過是從平劇表演程式中割裂下來的片段,如劍舞取自「霸王別姬」的「劍套」,帶舞取自「天女散花」的綢舞,翎舞取自西施,盤舞取自「麻姑獻壽」,其他如宮燈舞等,只是從翎舞中套出,換一換道具而已。而且這些動作的節奏與風格,和平劇表演體系是一致的,出現於戲劇,還不失其統一性,如果獨立的表演,便覺技擊意味多,舞蹈意味少,硬要說是我們的古典舞蹈,那只是在觀光藝術旗號下濫竽充數,拿來騙自己就太慘了。 誠然,真正中國的漢民族舞蹈,早已被外來舞所侵蝕,而逐漸不為人所喜愛。在戰國時,還有出名的趙國舞蹈邯鄲步(是否受胡人影響,像趙武靈王的服裝胡化尚不得知),在南朝的梁時,金陵還有「荊豔楚舞」的地方舞蹈(見庾信哀江南賦)。隋唐以降,只有外來舞占盡風光,今日文獻上保存的舞蹈名目,幾乎全部是外來的。也可說,唐以後從來沒見過中國內地任何地方有特殊的舞蹈。 漢民族的不重視舞蹈,也許和儒家的生活教條有關,儒家把音樂和舞蹈視為節制感情,調整生活的藝術工具,音樂與舞蹈成為「禮」的一部分,濃厚的道德觀念遮掩了音樂和舞蹈的原始情操,舞蹈變為揖讓進退的秩序表現,因之只保存於廟堂的儀節上,或祭祠大典上,有如今日祭孔時的八俏舞。這雖則也屬中國文化精神表現於舞蹈藝術的可貴之處,究竟這一類型的舞多屬?舞,表達的主題,過於抽象化與概念化,如果不由朝廷(政府)保存,民間無法表現整齊完美,雍容肅穆的意境;而且在民間這類舞蹈的應用也不廣,何況還得由各種音樂來伴奏,需要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大樂隊來執行伴奏任務,民間豈能辦到? 加之,自清代開始,我們的日常生活和音樂舞蹈,日行脫節,音樂與舞蹈逐漸轉入戲劇,成為表達故事的工具,而喪失了藝術的獨立性。民間所保存的,也只是迎神賽會的「獅舞」、「龍舞」等片段傳統舞蹈動作和殘餘的形式,所用的音樂,也屬舞臺敲擊音樂,曾經盛極于唐代的伴舞樂器羯鼓,宋代主要伴舞樂器篳O,只有在日本、韓國還保存著,我們早已採用較遲的樂器如嗩吶、胡琴作為最普通的舞蹈伴奏樂器了。 可是,要恢復古典舞風貌並不是辦不到的事,至少明代一部份的舞譜還完整的保存在朱載堉的樂律全書中,明代以上的舞蹈,也可以從日本、韓國拾回來一部分,雖則這些流傳到外國的舞蹈多少已異域化,變了些質,但較之我國自己所保存的較接近原始形式些,異域化的部分,我們自然該加以剔除,儘量恢復原始風貌。但恢復原始風貌,只能偏於精神的,形式上已沒有完整的直接材料可依據。所謂精神的,也只能從雕刻和繪畫上去捉捕,另如中古南朝迄隋北唐的壁畫和塑像,陶俑所表現的人物動作精神,而帶有濃重的感情成色,而參雜了印度、伊蘭、西域各民族的混合風格。漢代則從石刻上吸取古樸、單純的基調,想來大致不會差得太遠。 當然,我們絕不可ㄧ意的復古而忘卻了舞蹈也屬於感性藝術,內容必須反映作者的時代感受,形式也應當跟著世界性的舞蹈藝術潮流走,迂回而舒緩的農村社會生活節奏,以不足表達我們今日生活形態和意識,這正與中古時代的中國人,已逐漸對古樂與古舞冷淡,而接受外來樂與外來舞一樣。看唐代大?繁弦急管節拍,最急促時,他們稱為「入破」的當口,舞者才入場,已顯示他們對迂緩的樂舞不耐煩。中古如此,何況今日。 因之,我們的任務,似乎應當從恢復古典舞,認識古典舞,進而創造自己的時代舞。恢復古典舞,也應區分表現崇高道德意境的純樸族古代舞,和代表中古時的摻雜有外來成份的,以感情為主的隋唐時代舞。正如隋唐時代把「清商」和「燕樂」分開一樣,時代舞則不妨採取芭蕾的舞步技巧,融合東方的偏重於手勢表演藝術,使之成為真正能代表中國精神的舞蹈,把一向在平面發展的中國舞蹈立體化起來。 這些工作並不是沒有人做,好些舞蹈家已從事這項工作,我所知道得較多,認識較深的有好幾位,像劉鳳學女士、黃忠良先生夫婦全屬於從事這項工作最努力而有成就的。劉女士的研究路線是從日本、韓國拾取我們所遺失的部分,加以爬梳、整理,恢復原來風貌,再創造新型中國舞。黃忠良夫婦是吸收尚保存於我國的殘餘部分,用來豐富他們所專攻的現代芭蕾,使它成為中國風格的現代芭蕾。 由於他們這份辛勤的工作,我相信我們的舞蹈藝術,不久會有極突出的成就,和我們的音樂、繪畫、戲劇、雕刻齊頭並進,和諧的創造一片藝術新天地。一個民族的藝術復蘇,決不容那一項藝術一枝獨秀,或一干偏枯的。
|